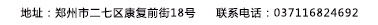|
哲学家培根认为有三种不同的研究人员:有人像蚂蚁一样寻寻觅觅、忙忙碌碌,但他们仅限于收集和搬弄材料,不能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像蜘蛛,沉湎于思辨玄想,凭空吐丝织网,他们的想象尽管美妙,但毫无实用价值。培根称赞像蜜蜂那样工作的科学家,“从花园和田野里面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以酿造出香甜的理论之蜜来。 其实,蜜蜂式人才的工作过程,只不过是归纳法的形象解说而已。对培根这个归纳万能论者来说,蜜蜂的方法自然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了。而当时法国科学家笛卡尔鼓吹的演绎法,依哲学家看,只能像蜘蛛那样徒劳无功了。培根和笛卡尔的分歧主要在于:培根主张自下而上的建构,由大量的经验概括为若许命题,并上升为笼盖全般的最高公理。而笛卡尔却倡导由上而下的方法,由公理演绎出命题,并解释变幻纷繁的各种现象。 这两种各执一端的方法,其实都只有局部的真理,在实际的科学发现、研究过程中,不仅需要归纳、需要蜜蜂式的人才,同样也需要演绎、需要纯粹的收集鉴别,即蜘蛛和蚂蚁式的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培根本人在科学上一无贡献,而笛卡尔却在物理、数学和生理学等几个方面成果累累。 下面,我们从科学家的秉赋、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这样三个角度,来详细谈谈蚂蚁和蜘蛛式人才的差别。 首先,我们从科学家的秉赋看,有些人长于发现、鉴别,适合做蚂蚁式的实验家,有些人长于玄思、猜测,适合做蜘蛛式的理论家。例如丹麦天文学家第谷,他是个极其勤勉的观察者,几乎毕生不厌其烦地以空前的精确度记录着行星的运动。当时还没有发明望远镜,他的数据误差几乎达到了肉眼观察的极限,比大名鼎鼎的哥白尼的数据精确20倍。他还发现了许多天文新现象,如黄赤交角的变化、月球运行的二均差,并测定了岁差。在观察上,第谷是一流好手,但他酿不出蜜来,他搞的太阳系折衷理论,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只是率领其他行星围绕地球运转。这个学说,比哥自尼倒退了一大步。相反,第谷的继承人开普勒却是发散型思维的科学家,典型的蜘蛛式工作者。开普勒是近视眼,不适合于搞天象观察,他在第谷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整天沉溺于虚构计算,神驰于组合推演。开普勒先入为见地认定当时已知的6颗行星和太阳间的距离具有一种规则的关系,他时而用音阶去拟合,时而又用几何形体的关系去拟合,直到得出著名的行星运行三大定律为止。也就是说,他的“蛛网”最终还是把太阳系给“粘”住了,而被人们誉为“天空立法者”。开普勒的工作,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础。 再从科学工作的性质来看,学科不同,在方法上往往也有不同的要求。对大多数化学家来说,要寻找新的元素、矿物,无非是无穷无尽的筛选试验、精炼测定:生化学家也许提炼出一种酶吧,那么主要工作也许是很枯燥乏味的,他要尽可能地测定大分子的化学成分和三维结构,纯粹是事实材料的收集和发表;而医生要研究疾病过程,也意味着解剖成千上万的动物,长年累月戴着透镜干极单调的工作。难怪爱迪生要说,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了。但是有一些学科.例如数学就不同了.常常需要蛛蜘式的人才。数学天才往往是早慧的,他们凭一支笔、一只圆规和一把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需要到事实的花园采集经验的花粉。印度数学家斯里尼哇沙·拉玛努贾的一生就是明证,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却独自巧思构想,写下了许多预言般的数学公式,在无穷级数、椭圆积分、无穷乘数、数论等方面的深刻见解,使世界数学界都为之震动。 最后,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当一门学科还处于“襁褓”阶段,人们的工作往往就只能是蚂蚁式的,只能做做收集材料、鉴别比较、命名整理等琐碎的事务。正像美国安大略科学中心主任威尔逊说的那样,地质学研究在开始时,不过是带着地质锤和六分仪跋山涉水,拾取岩石而已,“有点像集邮”。再比如超导领域是当代科研的一大热门,但就像我国超导专家指出的,目前寻找高转变温度超导材料,基本上是“炒菜式”的,淡了加把盐,成了泼勺水,大多凭经验和运气。有什么办法呢?没有长期的材料积累,没有蚂蚁式的带点盲目的忙碌,一门新学科不会像蘑菇一样,一场雨后就从地下冒出来。它要漫长历史的酝酿,也许是几代人的努力。苏联有位组织学家聂佛梅瓦基,有人问他怎么一生都在研究蠕虫的构造,科学家很惊奇:“蠕虫那么长,人生可是那么短!”这或许说明了科学工作的艰辛,走向辉煌的顶峰除了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几乎无限的耐心之外,时势也是造就英雄的必要条件。 而当一个学科进一步发展,进入像著名的科学史家库恩所说的“革命”阶段,蜘蛛式的工作者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爱因斯坦就是非常标准化的“蜘蛛”,他认为纯理论工作者一般采用的方法是,“他们总是从某些最一般的原理出发,从它推出个别特殊的结论,然后再把这些结论同经验相比较。”爱因新坦的观点,和笛卡尔是大体一致的。不过爱因斯坦还补充了经验和理论间关系的缺环,他在给好友的信中描述了下面这样的科研途径:爱因斯坦认为,经验和公理、命题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道路,只有直觉才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因此,很多科学家都承认,追求理论本身的简单、和谐,这种美学的考虑往往是科学创造工作的直接动机。后来,大哲学家波普尔根据爱因斯坦的观点,发展了一套比较成熟的逻辑体系。他认为,单称陈述的堆积是不可能演变为全称陈述的,或者说,即使观察到千万只天鹅都是白的,也不可能合乎逻辑地得出“凡天鹅皆白”的结论。这一学说宣判了“归纳万能”的破产,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总结和出发点。 不过,在需要创造性工作的领域内只干些蚂蚁的工作,或者在学科建立的准备阶段,便似蜘蛛般构筑庞大的体系,这自然另当别论。在一般的情况下,在科学发展的“常规”时期,蜜蜂式的人才就比前两者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了。培根的比喻,由于拥有相当的覆盖面,因而,便使人容易忽略蚂蚁和蜘蛛式的工作了。然而,正像伽利略说的,地球毕竟是转的,科学共同体内不仅存在大量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者和思入化境的天才理论家,而且各自都有着特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赞赏 长按
|